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观点辨正范文(7771字)
【内容提要】近年来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理解,存在着几种片面的、错误的观点,诸如将马克思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相混淆并主张过时论,将唯物辩证法意义庸俗化、方法论化以及实践本体论观点等。对这些观点进行辨析,以澄清思想上的错误认识,十分必要。目前较能体现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意图的惟有实践唯物主义(或辩证的、实践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但实践唯物主义在论证上仍然存在理论的缺环,需要进一步确立有关的科学基础,其中关键是科学而辩证地阐明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图景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 键 词】本体论/世界图景/实践/意识/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6198(2000)05—0011—06 目前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理解存在几种不同的看法,虽然几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它们之间的分歧既明显又尖锐。这种笼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上的迷雾如果不能得到进一步的澄清,可能会模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象,妨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的正确把握。要坚定唯物主义信念,从理论上看,有必要针对几种主要的理论见解做一点辨析的工作。 1 第一种观点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相混淆,认为唯物主义过时了,因此,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持这种理论观点的人,通常对所谓一般的唯物主义(或“物本主义”)不以为然,并且把这种唯物主义当作整个唯物主义的主要形态,没有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一般的物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区分开来。他们将对物本主义的否定与批评简单地转移到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否定与批评上来,认为既然物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已经过时了,那么,包含这种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过时了,因此,应当寻求新的解释立场。我们不排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个别言论带有一般旧唯物主义的痕迹,因为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时代,正是这种唯物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他们的某些话语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印记,受到时代条件的约束。同样,我们也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后继者如第二国际的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他们站在一般的旧唯物主义的立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这种情况,甚至在前苏联20年代以布哈林为代表的“机械论派”中也有所反映。他们受逻辑实证主义及物理主义的影响,寻求将复杂的、高层次的事物还原为更简单的、低层次事物的还原主义解释立场。我国的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受前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难以划清甚至模糊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界限的问题。实际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创立伊始就告别了旧唯物主义,并明确清算了与旧唯物主义之间的理论关系。我们知道,旧唯物主义在哲学本体论上的最重要的观点是,世界是由纯粹的无生命的物质及其运动构成的,其口号是:“给我物质和运动,我能创造整个世界。”这种唯物主义以近代自然科学为根据,对自然的世界图景作了机械论的描述。虽然与神学、唯心主义相比,它有一定的进步性与合理性,但它毕竟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特别是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以极为思辨的方式阐明了被机械唯物主义者们忽略的东西。然而,在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仍然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黑格尔辩证法被轻率地抛弃了。马克思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与超越者,吸取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打出新唯物主义的旗号,首先超越的就是这种纯粹的唯物主义。其代表人物当时是摩莱肖、毕希纳和福格特等人。福格特说:“思想对大脑的关系,有如胆汁对肝脏或者尿对肾脏的关系一样。”(注:k·c·巴克拉捷.近代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史纲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3.)没有肝脏就没有胆汁,没有大脑就没有思想。他们认为,生物界现象要用物理学和化学元素原理来说明,整个世界,无论是有机界还是无机界,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同一个原子,今天是粪肥的成分,明天可能同与它类似的原子一起组成芬芳的花朵。在他们眼里,世界无非是一堆原子,无机界与有机界并无实质的区分,精神也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物质或物质的机能。这种唯物主义将林林总总 的世间万物归结为一种物质即原子,认为一切都可以从世界的原子或物质构成中得到说明。他们不了解,生命的出现和精神的出现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事件,它们一经产生就既不能被还原也不能被取消,并且构成了由低到高的自然等级序列中的新层次。这种唯物主义没有看到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等级层次,没有看到高层次的等级层次具有低层次的等级层次所不具有的属性。的确,马克思认为精神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脑的机能,是物质世界的反映;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此,他不仅指出了精神自诞生起就具有的社会特质,而且进一步指出了精神对物质的能动的反作用。马克思在其本体论中明确肯定意识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的第二性的地位和作用,肯定人类意识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并把它纳入其辩证的世界图景之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要求把事物、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或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本身就明确地包含着肯定人的意识的能动性和因果作用这一理论环节。如果缺少了这一环节,人类能动的改造世界的活动就成了一句空话。在理论上,它是理解马克思实践观的基础,否定意识必然否定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否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何可能性。马克思多次明确地表示,他并不反对“精神的动力”,而是要进一步探索“动力”的动力。肯定意识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的第二性的本体地位和作用,是马克思扬弃唯心主义、超越旧唯物主义的重要环节。但马克思是在肯定自然界的先在性、第一性的前提下,肯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或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因而其观点与认为精神是世界本源的唯心主义有根本区别,与旧唯物主义的立场既有一致之处,又有重大差别。这种差别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从前的唯物主义”的差别,是辩证的、历史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与“纯粹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差别。因此,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等同于一般唯物主义或“纯粹的唯物主义”是断断不可接受的。 即使是对于一般唯物主义,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断言其过时。实际上,从17世纪以来,唯物主义在西方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哲学中,便逐渐占据了主导的地位,成为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19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更是如日中天,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唯物主义一直是西方科学及科学哲学中的主流。70年代以后,肯定突现与层次以及“下向因果作用”的非还原的唯物主义才崭露头角,逐渐取代传统的一般唯物主义,确立起新的主导地位。这种一般的或纯粹的唯物主义虽然已经成了少数派,仍然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哲学世界观和科学研究纲领,从物理主义到澳大利亚的唯物主义,到以丘奇兰德夫妇和克里克等人为代表的神经科学和生物学领域的唯物主义,都秉承了这一传统。它们至今仍然活跃于当代科学和哲学的前沿领域。无论如何,唯物主义过时论是不符合事实的。 2 第二种观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庸俗化,未能真正理解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导致辩证法的真正意义在理论和常识层面的失落。 辩证法首先是一种世界观。尤其是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与世界观是紧密结合的。马克思的辩证法也同样吸取了并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本体论辩证法立场。作为世界观的辩证法,它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揭示了辩证的世界图景,而不仅仅是被后来的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教条化了的所谓两大原则、三大规律和一系列范畴的组合。世界观的辩证法是对辩证的世界图景的总体把握,这个辩证的世界图景是自然、社会及其历史的立体动态图景。在黑格尔那里,这个图景是头足倒置的,是以绝对精神为中心展开的。马克思把它倒了过来,并且唯物主义地阐明了自然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这种新唯物主义的世界图景中,物质自然界处于最基础的地位;依次往上,随着地质历史的演化,出现了生命;在生命的基础上,出现了具有高级精神智能的人类,历史从此由自然史演进到人类史,并且通过人类的创造活动衍生出人类诞生前自然界所没有的人化自然。具有精神的人和人类社会的诞生是自然进化中的一个伟大质变。马克思敏锐地把握了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的辩证等级和层次,他不仅清楚地看到了从无生命的自然到有生命的自然、再到具有精神的人和人类社会与历史这一由低到高的既有普遍联系又有重大质的差别的发展过程,而且明确指出,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是对更高层次的人类社会和历史规律的揭示。在他的自然—社会本体论框架中,一个关键的理论环节是:承认人的精神、人的活动和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实在性和辩证的层次性,承认它们不仅源于自然,而且高于自然,不仅与无生命的自然物、与有生命的自然物有质的区别,更主要的是它们对低层次的事物起一种宏观决定或下向因果作用(开放的历史决定论),这是马克思超越旧唯物主义、确立新唯物主义的自然—社会的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基础,是他在哲学上实现革命性变革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前提。唯物辩证法的规律与范畴只有紧扣这一辩证本体论框架 才能得到最具体、最有生命力的展开。离开这个辩证的世界图景,离开这一质的规定性,进而把辩证法仅仅理解为一种方法,无疑会导致辩证法意义的失落,这一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总体的辩证法就会失去应有的光彩。 传统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恰恰未能紧扣这一主题,而是简单地将唯物辩证法圈定于辩证自然观,而且其物质范畴往往过于狭义,忽略了物质的多层次的其他形态。因此,一些人诟病辩证唯物主义,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强调自然的物质方面,而在于如何辩证地理解自然与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世界图景,这恰恰是马克思超越前人的最有贡献的方面。马克思出入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及其辩证法,其所继承的理论遗产决不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辩证法,而且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经过新唯物主义洗礼的辩证法,即新唯物主义的辩证的世界图景理论。辩证法固然是一种方法论,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断不可将辩证法方法论化。世界观、本体论的辩证法是硬币的另一面,甚至是更重要的一面。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一种世界观的辩证法,是一种头足倒置的世界观或自然历史观,在他那里,自然是历史和绝对精神的外化、生成过程。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巨大价值,并将它颠倒过来,加以扬弃,创立了唯物的历史的和实践的辩证法。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按其本质来说是本体论的辩证法”(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13.),不只是存在于历史和意识领域,而且存在于自然界中。正是由于自然界的辩证运动,才在对立统一、量变质变等运动中产生了形态和性质各异的种种新事物,产生了发展的阶梯和新的质。自然界不仅存在着飞跃,而且正是由于这无数的飞跃才构成了发展的链条,并且盛开出了人类精神这朵鲜花。人类精神倾注在劳动实践当中,体现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当中,一步步地创造出人类的历史和社会。自然界的生物进化逐渐让位于人类精神和文化的进化,自然史也逐渐地过渡到人类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自然—历史的总体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一种辩证的自然—历史的唯物主义。由于马克思侧重研究的是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过程及其规律,因此,我们也可以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简称为历史唯物主义。 3 第三种观点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归之于实践本体论,最终导致实践唯心主义。 与以往的哲学相比,马克思更重视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可以称之为一种改造世界的实践哲学,是一种实践唯物主义,但不能将它归结为实践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的核心原则是强调实践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回避乃至否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这是一条反唯物主义的原则。虽然马克思哲学的重心不在于阐明自然界的辩证法,而在于阐明社会实践领域的辩证法,但这并不等于可以否定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很显然,实践本体论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质的弘扬是以牺牲唯物主义为代价的。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源于一般唯物主义,但高于一般唯物主义,这是不争的事实。实践本体论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架空起来,并将它整个地安放在一个并不牢靠的流沙基础上,其用意虽然是突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质,但不管怎么说,否定马克思哲学的自然本体论基础,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大厦也将摇晃。事实上,强调人类实践活动与坚持唯物主义并不矛盾。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已经有了质的区别。实践本体论对此却恰好缺乏体察。诚然,在一般唯物主义或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中,是没有作为主体的人和人的实践活动的位置的。说它是物本论唯物主义也不为过。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已经从根本上超越了这种物本论唯物主义(或客体唯物主义)。在这种新唯物主义的世界图景和本体论框架中,自然与社会、物质与人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它们之间既有连续性,又有间断性和飞跃,既有彼此间紧密的相互作用,也有性质迥异的区别。而有精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或意向行为),是这种新唯物主义框架中最富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质的方面。这一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质不仅被“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抹去了,而且也被实践本体论者们忽略掉了。 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这种错误并不新鲜。19世纪,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并没有立刻引起德国思想界的普遍重视。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以抛弃辩证法为代价的纯粹的唯物主义占主导地位,这种唯物主义师从达尔文的渐进进化理论,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坚持还原论,在社会领域则主张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19世纪后半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些达尔文主义的拥戴者也遵循着这条思路,认为马克思反对精神、观念的作用,只主张经济决定论。他们不理解唯物史观的真正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崛起,正是直接针对这一状况的。他们倡导“回到黑格尔”,实质上是要回到辩证的总体性和主体性原则,并最终回到历史的、社会实践活动的辩证法。直至今天,西方人所理解的唯物主义( 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仍然是严格的唯物主义,即物本主义。实践本体论者也在此处失足,说明他们同样不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真正意义。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连唯物主义都不是,而是实践人本主义,马克思新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的新形态,而是人本主义的新形态(注:丛大川.是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还是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a〕.任平,王金福,王晓升. 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c〕.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852—858.)。这种将唯物主义与人本主义对立起来的做法,实际上只是正确地揭示了西方哲学话语中的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的不足,由此得出马克思新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的论断,实在是张冠李戴。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真的会妨碍其人道主义理想的阐扬吗?当然不会!因为这种新唯物主义是内含着人类精神和实践的实在性和能动性的辩证法。后者不会因为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承认自然规律的基础作用而受到任何限制。相反,离开了这个基础的人本主义精神倒成了无根的浮萍。试想,在人类精神和价值以及人类实践活动本身的本体论地位尚未得到肯定的条件下,人道主义理想充其量只是一种美丽的幻影或精神泡沫。况且,人道主义理想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实证展现,离开了社会历史领域的主客体遵循一定规律的互动过程,离开了历史的唯物主义,它又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恩格斯的合力论早已明确表示了对线性决定论的反对,人类历史的合目的性早已超越了传统唯物主义的樊篱,而且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主张或赞成过庸俗化的经济决定论(恩格斯在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中一再表明这一点),这也正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高明与创新之处。这一切都可以在新唯物主义的框架下实现,抛弃这个框架,只能说明论者们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理解失当,并因此导致对整个唯物主义理论的错误估计。 4 第四种观点是正确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但论证的范围狭窄,未能真正确立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 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完全正确的,这种理解摆脱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化、机械论化的错误,同时也与实践本体论划清了理论的界限。但如何将自然、意识、实践与社会历史等方面统一起来?如何恰当地把握马克思的辩证的世界图景?尤其是如何确立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这仍然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过去我们比较侧重于从社会历史的方面来说明其科学性。这固然是重要的。但人类实践本身为什么是能动的?它的能动性来自于哪里?为什么意识具有能动性和反作用?意识作为实践的重要环节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在理论上,我们以往对此并没有清楚明确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时代也不可能回答这类问题。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有必要确立科学的本体论立场,使实践的唯物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因为作为世界观的唯物主义决不可能与科学相脱离。近代自然科学强化了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但同时也将片面性带入了唯物主义。由于它不了解人类社会与纯粹自然领域的质的差别,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采取了还原论的机械唯物主义立场,不能够将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因此,这种唯物主义多半是半截子的。经过历史辩证法的洗礼,唯物主义实现了巨大的跃进,确立了新的辩证的、历史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但这种原则立场在很长时期以来被人为地与不断发展的科学隔绝开来了。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长期囿于经典机械论的世界观框架,消极阐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未能从总体世界图景的把握入手揭示新唯物主义的实质的革命方面,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 实践唯物主义的出现,是对这种倾向的富有建设性的矫正。但实践唯物主义本身仍然存在如何说明实践的关键环节——意识——的科学地位和能动作用问题。从本体论角度来看,这是我们必须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而它恰恰又是当代科学(物理学、神经科学和意识科学等)正在探索的前沿问题。当代西方唯物主义面临的最大的理论课题就是如何科学地说明意识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即所谓的“布伦坦诺问题”(注:布伦坦诺问题,也称为布伦坦诺论题(brentano thesis), 原指人的意向性问题,德国哲学家布伦坦诺以意向性为基础对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进行了区分,意向性后来成了现象学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在当今的意识科学研究中,人们常用布伦坦诺问题来泛指一切关于“有意识的经验”问题或“意识之谜”。1994年,美国哲学家查尔默斯将这类问题概称为意识研究中的“困难问题”。))。如何从科学和哲学的角度进一步阐明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这是需要下大力气来做的一项宏大工程。它事关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事关新的科学研究的指导原则,事关两个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事关知识、智能经济时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创新,我们没有理由将我们的认识停留于实践一般的笼统阶段。如果我们能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广泛吸收当 代世界唯物主义和意识科学研究的积极成果,在科学的、创造性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确立实践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历史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将拥有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更广泛的启示力和吸引力,唯物主义的信念将更加牢固。
1FWA范文链接:http://www.1fwa.com/fanwen/149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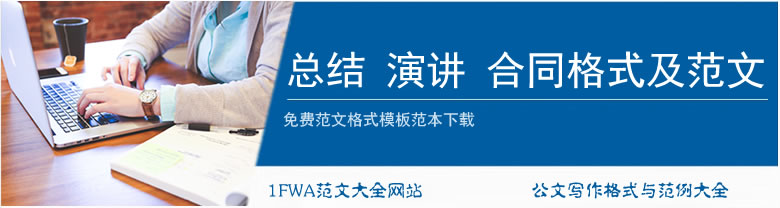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哲学范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范文